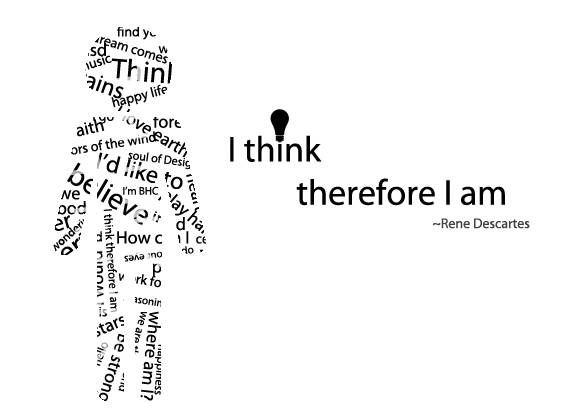
哲学史学习笔记(三) 近代哲学3 唯理论/理性主义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正值西欧剧变,市民阶级、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封建王权、新教、天主教,各派势力在这片土地上明争暗斗,整个欧洲混乱不堪。其中,最值得主义的一对矛盾是,资产阶级已经积蓄了足够多的力量,开始登堂入室,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取代日薄西山的封建王权,其标志性事件有二:一是荷兰通过内战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二是十七世纪的英国的一系列内战,以及后来的光荣革命。这两个国家思想最为开明,成为近代欧洲新哲学急速发展的桥头堡,也先后成为世界的霸权国家。
资产阶级甫登大位,亟需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理论来帮助统治。前期,文艺复兴对于人类思想进行了彻底解放,其核心“人文主义”将人的主体性提升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同时,科学(自然哲学)的蓬勃发展让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是由各种奇迹或者神迹组成的,它的运行机理可以被人用理性所认识和把握。这使得人们重拾对于人类理性的信心,致力于启发人类智慧,开启了后续被称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运动。
自此,认识论的研究成为哲学的主流,人们开始研究人类如何能够更好地认识自然。西方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主要分为了两个流派:一是经验主义(又称为经验论),二是理性主义(又称为唯理论)。
在主流的观点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才被看作是近代哲学的开端。但是这两个思想流派本身又有其发展脉络和历史沿袭,其中不乏哲学史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伟大人物,所以本系列的近代哲学章节用了两个章节作为铺垫,才引出作为主角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唯理论/理性主义
唯理论各大代表人物均是欧陆哲学家,又被称为大陆唯理论。理性主义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的古老传统,为了区分,也可以将这一派称为现代理性主义。
唯理论哲学家大多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深厚的宗教背景,这塑造了他们的形而上学底色,同时继承了经院哲学中的神智学传统;二是极高的数学造诣,使得他们像追求数学的普遍性一样,强调人类理性的普遍性。因此,我们在了解理性主义观点时,时常能看到古希腊哲学体系的影子。
笛卡尔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年3月31日 - 1650年2月11日),生于法国卢瓦尔省的图赖讷镇(现改名为笛卡尔镇)一个旧贵族家庭,天主教徒,近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代表作有《第一哲学沉思集》《哲学原理》,其他著作有《谈谈方法》《论灵魂的激情》等。
笛卡尔年轻时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位于拉·弗莱的欧洲顶级学校皇家亨利·勒格兰德学院,接受了完整而深入的贵族教育,成绩优异,涉猎广泛。后来,他对当时的经院哲学教育感到失望,于是放弃了书本学习,投入社会,研究更加现实的问题,特别是数学和科学问题。
笛卡尔曾入伍参与三十年战争,后游历欧洲。由于法国教会势力强大,笛卡尔担心会受到类似伽利略的迫害,所以迁居荷兰,在荷兰著述他大多数的哲学和科学研究成果。笛卡尔的著作一度被列为禁书。后来受聘前往瑞典,成为瑞典女王的科学顾问,最后因为无法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工作环境而病逝。
形而上学
人们一般将笛卡尔看作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是因为他提出了近代哲学最重要的原则:思维原则,即哲学是以人的思维为第一研究对象的。
在笛卡尔看来,形而上学是一切科学的根,物理学是科学的主干,其他科学则是繁茂的枝叶,只有牢固的形而上学基础才能够支撑庞大的科学体系。基于对数学和几何学的研究,笛卡尔认为哲学也应当像数学那样建立一套公理体系,从无可置疑的前提出发,逐步建立起整个理论大厦。而当时的经院哲学已经失去了作为基础的能力,因此笛卡尔要在经院哲学之外,重新建立一套形而上学。
此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提出形而上学的公理,也就是“大前提”。在笛卡尔看来,形式逻辑只能基于已有的知识进行形式上的分析,而不能得到新的知识。推理方法无法给出前提,那么就需要理性自身来给出前提。他提出基本原理应满足两个条件:
- 它们必须是明白而清晰的,人们在思考它们时不应有任何的怀疑。
- 人们关于其他事物的认识应当是完全依赖于这些基本原理的,这些原理本身可以独立存在,但脱离这些原理,人们就不能知道其他的任何事物。
笛卡尔将观念分为三类:一类是天赋的,一类是外来的,一类是自创的。外来的观念依赖于感知,自创的观念借助于想象,而天赋观念来源于纯粹的理智,才可以成为一切知识的思想前提。
我思故我在
为此,笛卡尔采用了怀疑主义的方法论,他说:
如果我想在科学上建立某种可靠、恒久的东西,我就必须认真地把我所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
此处的怀疑首先是对本体论本身的怀疑。对于任何可被质疑的对象,笛卡尔都采取的“悬置”的态度,包括感觉经验、可能在梦境中呈现的事物、数学,甚至上帝也是可以怀疑的。排除一切干扰项后,唯一无法排除的,就是“质疑”,或者“排除”动作本身。因此得到:“我在怀疑”本身是无可置疑的。
纯粹的否定姿态反而能够萌生出最凝练的确定性,此处的“否定”成为了“存在”的构成性例外,一切将以它为基础而存在。
笛卡尔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区别在于,怀疑主义的怀疑是主动的,是目的,而笛卡尔的怀疑是被动的,他是为了停止怀疑而不得不怀疑。
笛卡尔的出发点和培根实际上是相近的,但是走的路却截然相反。
而“怀疑”这个动作本身必然需要一个主体,那么这个必然存在的主体就意味着:
Cogito ergo sum.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
这句话的中文翻译容易引起误解,似乎“思”与“在”是因果关系。然而“思维”和“存在”本身是异构的,二者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不存在先有某物而后有某物。但这不妨碍它们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才是这对二元组的本质。刨除了一切可能外在于“我”的事物后,唯一依旧无法和“我”分离的,是“思维”,“我”是一个心灵实体,“我”即是“思维”。
进一步地,正是由于“思维”地存在,使得除它以外地东西不再可靠。剥离和抽象恰恰是纯粹思维的功能。
这句话清晰地确立了主体性的本体性地位,外在的事物是可怀疑的,而内在的“我思”是不可怀疑的,具有超越性,成为本体论的发生基础。同时,一切的知识都应以人的存在为前提,这也是笛卡尔认识论的出发点。
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将笛卡尔看作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我们且不说唯心和唯物的二分是否适用于笛卡尔。在笛卡尔之前,一切的哲学本体论都是建基于某种臆想的客观实在上的,而笛卡尔第一次以“思维”作为本体论基础。相比于前人杜撰的客观实体,“思维”本身是更加确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其他本体论前提
通过怀疑,笛卡尔确立了“我思故我在”的原则,但无法得出其他任何结论。笛卡尔借鉴了安瑟伦对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怀疑的方法如此有效,说明“我”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但“我”的心中却有一个无限完满的上帝概念,这个概念必不是来源于“我”,而是来源于“我”以外的一个完满存在,这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必然存在。
应当注意的是,“上帝必然存在”这一结论的前提是“‘我’是有缺陷的”。同时,为了避免一般形而上学可能导致的无限后退的 bug,笛卡尔提出上帝就是“第一原因”,即“上帝自身存在的原因是其自身”。
彻底的怀疑导向彻底的存在,这是魔法般的操作,笛卡尔不敢相信(或者不敢宣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做了一点概念偷换。如果笛卡尔能够坚持“我思故我在”,他会说,思维才是自身的原因。
但是,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三个沉思“论上帝及其存在”中,他写道:“如果我不依存于其他一切东西,如果我自己是我的存在的作者,我一定就不怀疑任何东西,我一定就不再有希望,最后,我一定就不缺少任何完满性;因为,凡是在我心里有什么观念的东西,我自己就会给我,这样一来我就是上帝了。”
笛卡尔提出,人可以通过身体感官来获取感觉,这种“感觉”必然是由于某种外在于心灵的力量所引发的,因此物质世界(非心灵的物体)的存在是其无法否定的。心灵和物质作为有限实体相互独立又相互对立,但二者又无法单独存在,需要上帝这个无限的实体给予协助并居中调和。
以上就是笛卡尔为形而上学提出的三条公理:我思故我在、上帝存在、物质世界存在。这构成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的本体论体系。
但是心灵实体和物质世界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心灵实体(人)是不整全的上帝,而物质世界必须依靠于上帝才能存在。这就使得物质世界不再具有本体性地位,而成为心灵的某种附庸。因此,人类理性所构造的符号学体系(数学、物理学等等)才可以用来描述物质世界。
同时,笛卡尔承认人类的有限性,认为人类不可能理解上帝本身,这使得他很巧妙地绕过了神学家的领域,避免陷入神正论或自由意志之类的神学死胡同,使得人类可以从心灵出发直面物质世界。
进一步,由于心灵规定了物质世界,那么由人类理性所认知的物质世界就是整全的。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物质世界也就必然是有限的。而物质世界本身也会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而变化。换言之,在物质世界中,人类已经是全能的了,人类的使命,便是不断地拓展自身的理性,进而丰富物质世界的面貌。
在这一意义上,现代自然科学几乎全都运行在笛卡尔主义上(除了量子力学等极少数领域)。
心物二元论
我思故我在确定了思想实体的存在,上帝保证了物质世界(广延实体)的存在。对于物质世界,笛卡尔的观点是纯粹机械论的,他说:“给我物质(广延)和运动,我就给你建造世界。”
不愧是发明了解析几何的人,可惜当时没有《三体》给他看。
人是思想和物质的复合实体。对于二者的关系,笛卡尔优先考虑心灵,并认为心灵可以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但身体不能没有心灵。笛卡尔困惑于身体和心灵如何保持同步,他提出可能是由大脑中的松果体来连接身体和心灵。
笛卡尔曾在其《沉思集》中讨论,为何上帝要创造“人类”这样一种有缺陷的、不完善的物种,最终没讨论出个结果,并认为这就是人类不完善的体现,人类的心灵和肉体都是有缺陷的。他认为,上帝已经给予了人类理性、智慧、自由意志等能力,只是人类无法有效运用它们。
笛卡尔认为只有人是具有灵魂的,否认动物具有理性或智力。这个观点成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后来被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所否定。
这种尝试使用理性来对灵魂进行研究的做法消解了灵魂的神圣性。为了避免受到迫害,他曾推迟部分著作的出版。但他后来还是被指责为宣扬无神论。
心物二元论观点来自于托马斯·阿奎那,是笛卡尔主义中一个明显的破绽,也是近代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中学课本马哲中提到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来源于此。
笛卡尔的几条推论中,除了“我思故我在”这一条外,另外几条的论证都十分牵强,处处是偷换概念和逻辑短路,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科学贡献
笛卡尔是中学教科书中的人物,在数学、物理学等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包括但不限于:
- 建立笛卡尔坐标系,创立了解析几何。
- 首次较为完整地第一次表述了惯性定律:只要物体开始运动,就将继续以同一速度并沿着同一直线方向运动,直到遇到某种外来原因造成的阻碍或偏离为止。
- 论证了光的折射定律。
- 提出了动量守恒概念。
- 提出了天体演化和漩涡模型。
- 提出了神经系统的反射理论。
- 首次在出版著作时采用了同行评议。《第一哲学沉思集》出版前,笛卡尔将此书发给多位哲学家与神学家阅读,随后收到了六组反对意见,笛卡尔将这些反对意见和自己的回复收录在书中附录一同印发,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同行评议。
斯宾诺莎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年11月24日 - 1677年2月21日),葡萄牙裔犹太哲学家,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理性主义先驱,17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代表作有《伦理学》《神学政治论》,其他著作有《笛卡尔哲学原理 依几何学方式证明》《知性改进论》《政治论》《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以及若干通讯等。
为避免天主教会对犹太人的迫害,斯宾诺莎的先祖移居荷兰。斯宾诺莎受到同在荷兰的笛卡尔的影响,开始研究理性主义哲学。他对宗教发表了一系列激进观点,被认为是异教徒或无神论者,受到犹太教会的绝罚,并因此被阿姆斯特丹当局所驱逐。数百年来,犹太社区曾数次评估是否需要收回相关指令,但均被犹太教会高层否决。
斯宾诺莎靠研磨镜片为生,并因此过着简朴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工作时吸入了过多粉尘,斯宾诺莎于44岁那年死于肺病。
斯宾诺莎主义是近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一环,黑格尔有赞曰:“斯宾诺莎哲学是近代哲学的重点,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要么就不是哲学。”海涅也说:“我们所有的哲学家,往往不自觉地通过斯宾诺莎磨制的眼镜在观察世界。”
实体一元论
斯宾诺莎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他同样是从一个基本的原则出发构建哲学体系。和笛卡尔不同之处在于,斯宾诺莎的本体论出发点是对实体的定义(而不是思想),亦即宇宙万物的根本原因和最高原则。
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提出以下重要界说(定义):
- 自因是本质中包含存在的东西。
- 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无须借助于他物的概念。
- 实体即是自因。
- 属性是由知性看来,构成实体本质的东西。
- 样式是实体的分殊,即在他物内并通过他物而被认知的东西。
- 样式的本质不包含存在。
- 万物是展现神的广延属性的某种样式。
- 自由是仅仅由自身必然性而存在并由自身决定其行为的东西。
- 意志和欲望并非是自由,因为它们是由外因引起的。
上述定义推导出了若干命题,构成了斯宾诺莎地形而上学大厦。实体必然是无限的,任何有限的事物不可能符合实体的定义,因为有限的事物是受到他物的限制的,这些事物只能够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被认识,而且无法仅依靠自身来自我认识。因此,宇宙间只存在有唯一实体,它是绝对无限、自因,永恒、且不可分。斯宾诺莎称这唯一实体是“神”或“自然”。事实上,斯宾诺莎将这两个词语视为同义,他将其描述为“神或自然(拉丁语:Deus sive Natura)”。而“神或自然”所赖以存在的永恒无限的本质,就是必然性。
斯宾诺莎常被认为是泛神论者,从“神即自然”这个表述来看似乎确实如此,但应当注意的一点是,斯宾诺莎的“自然”是超越于物质世界的。
对斯宾诺莎而言,整个宇宙即是由唯一实体以及它的样式组成,万物都诞生自唯一实体并在其之内、依靠其而存在,因此一般称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为“实体一元论”。
笛卡尔的体系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只能够证明到“我思”的存在,而若要证明物质世界存在,就不得不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偷跑和逻辑短路,这才诞生了唯物和唯心的二元对立问题。斯宾诺莎发现,“我思”其实并非是本体论的前提,在“我思”之前,有一个更基础、更前提、更具有普遍性的东西,那就是“必然性”,存在本身也发生于它。于是,以此作为本体论的起点,就能够规避这些问题。
为克服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的缺陷,斯宾诺莎在本体论中将物质(广延)和心灵(思维)解释为实体的两个属性。理论上说,实体有无限多的属性,但人类理性能够把握到的就只有这两种。实体可从物质世界或心灵世界被认知,广延和思维代表了对物质或心灵世界的完整叙述。
斯宾诺莎提出,人是心灵和身体的同一,但心灵和身体不能互相干涉。人的心灵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而正确的知识(真知识或真观念)来源于神所蕴含的永恒必然性。因此,理性的本性就在于认识事物的必然性。
因此,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并不存在唯物和唯心的对立。
这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因为斯宾诺莎的哲学是以其伦理学为核心的。万物并非被动存在的实体,其中还蕴含着来自于绝对者的思维,物质存在本身就代表着神的“深思熟虑”。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黑格尔对斯宾诺莎评价那么高,因为他自己就是最大的斯宾诺莎主义者。
伦理学
斯宾诺莎认为圆满/不圆满、善恶的概念看作是人类思维的样式,并不代表事物的本质属性。所谓善,是就人类确知有用之物而言的,而恶是对善的占有的阻碍。
斯宾诺莎将人无法控制和克制情感的状态称作奴役,因为当人受到情感的支配,行为便无法自主,只能受到命运的宰割。他提出,符合人的本性就是善,最高的善乃是对神的知识,最高的德性便是认识神,只有遵循理性的指导,才能够有正确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统一和和谐,这样的人便是自由的。相反,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受到情感和欲望的影响,他的本性便会受到扰动,行为便会与其本性相悖。
综上,通向自由的道路,唯有按照理性的指导,去认识必然性。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其行为将符合自然必然性的要求,也不会受到外在的善恶观的影响,他将正直、诚挚、克制、智慧、勇敢,并且永远正确。当然,人是不可能真正自由的,那是神才能达到的境界,换言之,人永远在追求自由的路上。伦理学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核心,他将人类的道德、幸福、欲望、仁爱、虔诚等等统统纳入了理性的范畴。
斯宾诺莎提出,人应该按照理性追求自身的利益,因为当每个个体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人与人个体间也能达到利益最大化,因为经验说明,只有人与人互相帮助,才能各取所需,共同抵御灾祸。
这套伦理学是有致命弱点的。斯宾诺莎将一切矛盾视作实体内在的矛盾,不能解释的是,如果实体是圆满的,是绝对的必然性,那作为其属性要以表象世界的形式呈现出来?为什么物质世界是不完满的?为什么心灵会失去理性而收到情感的控制?事实上,实体和其分殊的二分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不可抵抗的不完满性,强行去解释,就会落入某种决定论和宿命论。
好在斯宾诺莎的宿命论不是古希腊悲剧里那种纯粹被动的宿命论,而是是宿命中人在知晓一切的前提下,自由地塑造自己的命运,因为人本来就是神的一部分,因此运用理性便能够一眼看穿那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人其实是神在必然道路上踏下的足印。所以,斯宾诺莎的自由,并不是任意行动的自由,而是对必然性、对自我最彻底的认识。
宗教观点
斯宾诺莎的本体论从根本上将神去人格化,认为神(自然)本身并没有任何目的性,对于人既没有爱,也没有恨,只是“神圣必然性”的体现。因为目的即是欲望,如果神是有目的的,那么神必然是欲求着其缺乏的东西,这就否定了神的完满性。因此,以神为目标的祭祀和奉献其实质都是迷信,是将人类的欲望和疯狂强加于神的行为。人格神完全是人类由于愚昧,为便于想象而创造出来的东西。
在“神正论”方面,由于善恶实质上是人类基于理性判断得出的普遍观念,而不是自然存在的物体,因此判断神的善恶本身是非法行为,因为在神看来世界并无善恶的分野。
《神学政治论》集中阐述了斯宾诺莎的激进神学观点,包括但不限于:预言家(即拉比)仅通过想象来解读神启导致启示暧昧不清,希伯来人并非唯一选民(上帝对所有民族一视同仁),宗教礼仪不是普遍适用而是由社会需要生成,以及《圣经》的考据成疑,等等。
斯宾诺莎很努力地想要在理性的基础上建构宗教大厦,并进一步为社会生活提供一套伦理规范的雏形。其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他被认为是无神论的主要原因。
斯宾诺莎并不是真的无神论,他只是揭示了有神论的矛盾:如果完满的神真正存在,那么一切的矛盾都将化为神的内在矛盾,不完满的事物会自然地与神同一。而那些宗教徒所坚持的,其实是不完满事物与神的二元对立。所以,黑格尔将斯宾诺莎称作“无世界论”。
莱布尼茨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又译莱布尼茨,1646年7月1日 - 1716年11月14日),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侯国的莱比锡,杰出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人类理智新论》《神正论》及若干论文、通信等。他深受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哲学观点影响,是继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后第三位重要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
莱布尼兹出生时,德国正因为三十年战争而四分五裂、千疮百孔,莱布尼兹的一大工作就是在各方势力间斡旋,特别是新教和天主教,试图实现宗教的再联合。同时他还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在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神学、历史学、语言学、信息科学等等诸多领域有所创建。
单子论
莱布尼兹要解决的问题依旧是物质世界和形而上学世界的矛盾。物质世界是由广延组成的,是无限可分的,然而实体是不可分的(实体如果可分,它就依赖于其部分而存在了),如果采用斯宾诺莎的理论,实体唯一,那么物理世界将成为实体的纯粹现象,世界的目的将会导向某种决定论和虚无主义。
因此,莱布尼兹并没有接受斯宾诺莎对于实体的推论(斯宾诺莎认为广延是实体的一个属性),他认为,实体应当具有这些特点:
- 实体是客观存在的
- 实体是其自身存在的原因
- 实体是单纯的(不可分的)
- 每一个事物都应当有其对应的实体,因此实体是无限多的
- 实体着某一个事物最精纯的一面,因此实体是纯粹的,没有广延的一面,因此它必然是非物质的,在数学中,实体意味着“0”
- 实体没有广延,也就意味着没有运动变化,也不会,因此是永恒的
- 不同的实体之间是相互不能影响的
- 每一个实体都是独特的,不同实体之间有质的区别(如果只有量的区分,那么就是可分的)
这些实体被称作“单子”(Monad)。单子是客观存在的、无限多的、不可分的、非物质的精神实体。
和斯宾诺莎一样,莱布尼兹把握住了笛卡尔理论中的缺陷。笛卡尔从“我思”出发,事实上是无法推导出物质世界的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只能够推导出其“必然性”存在,莱布尼兹的“单子”实质上就是物质世界存在的“必然性”。通过简单的形式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物质存在,其单子必存在;单子存在,相应的物质未必存在。
前定和谐
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单子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但是物质世界是相互影响的,那么物质如何与单子发生联系?
莱布尼兹提出“连续性原则”:单子并不连续,但是能够无限绵密地排列,任意两个单子都不是相邻的,而是间隔着无数多的其他单子。
感受到微积分的力量了吗?
举个例子:一片森林对应着这一个森林实体,森林中的每一株树木各自对应着一个树的单子,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对应着一个叶子单子,把叶子摘下来撕碎了,每一片碎片也都对应着一个叶子碎片单子。
单子的排列也并非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由高到低遵循了某种既定的顺序,来保证单子之间能够和谐地存在。决定这种排列的,是一个无限完满的至高单子,即上帝。上帝在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就已经保证了世界以一种最稳定而和谐的方式运行,再也无需进行干预,这就是“前定和谐”。
“前定和谐”也用来解释身心二元论问题,身体和心灵的同步是由上帝的预定和谐来保障的。也因此,莱布尼兹反对牛顿式的机械宇宙观,他认为神在创造世界时,这个世界已经足够精巧,无需祂通过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的方式来给世界的运行上发条。但是牛顿派反驳道,莱布尼兹只是用一个最大的奇迹来掩盖微小的奇迹罢了。
“单子”只是物质世界存在的必然性,要从必然性到现实性,就必须有一个超越性的力量去推动,这个力量就是神。“前定论”和“决定论”听起来有点相似,但有实质上的不同,“前定论”仅仅是在伦理学的层面确保了世界运行的和谐。
单子是封闭的,莱布尼兹实际上是在每一个单子上都单独运用了一遍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因此,每个单子都能够自我维持,但也因此,单子仅仅能够自我维持,因为它无力再去维持他物。这也是单子必须是思想实体的原因,因为“单子思故单子在”。
这里面有一个很小的bug,如果普通单子的存在都被那个至高单子所决定,那么就不满足“自因”的性质了。很难说莱布尼兹没有想到过这个,但是其宗教背景使得他不得不忽略这个问题。
单子的封闭性与“前定和谐”能够得到一个进一步的推论,即“每一个单子都像镜子一样独立地映射了整个世界”。如果将“前定和谐”视作是外在于单子的因果链条,那么整个世界的变化将通过链条的颤动传递给每一个单子。而物质世界,其实就是呈现在单子面前的世界映像。
所以,单子其实并非是单纯的,而是一系列自我封闭的内在规定性的集合。或者说,每一个单子都是孤立的小世界。这很像某些玄幻小说的设定。
这事实上就是康德的“物自体”,也有巴门尼德的“存在”的影子。归根结底,单子是纯粹的必然性,是不可见的。就像人眼看不到身体内部的器官一样,人类的理性单子也感受不到自身存在,其所能体验到的的,其他单子向外部展示的表象,也即“因果链条的颤动”。
同时,“前定和谐”莱布尼兹将伦理学上升到了本体论高度。因为单子仅仅意味着存在的必然性,神作为最高单子必然是道德的,因此所有单子的存在本身和其所折射出的世界表象也必然是真实的。
莱布尼兹的在描述“单子论”的时候,态度类似于他发明微积分,或者笛卡尔发明坐标系那样,是一种使用工具的态度。这些哲学家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本体论框架仅仅是用来解释世界地某种模型,而并非世界的“本来面貌”。
莱布尼兹形而上学体系分散地分布在若干论文和书信中,可阅读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的《新系统及其说明》和《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
认识论
虽然说每一个单子都是一种纯粹精神,但是单子和单子之间又有高下,高等级的单子对于低等级的单子具有统治力。人的理性单子(即“灵魂”)相比于那些“深陷于物质之中”的单子具有更高的完满性,就像是具体而微的神明一样。
在《人类理智新论》中,莱布尼茨继承和发扬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理论,认为人的认识必然来自于其内在而非感觉经验。但是这个认识并非是“生而知之”,而是根据人的理性单子的性质,以禀赋和潜能的形式体现,即“有纹路的大理石”,人可以顺着其“纹路”来塑造自身。感觉经验的作用就是去激发人的潜能。
人的理性单子其实就是人的先验范畴体系,是人认识世界的能力基础。“前定和谐”所“前定”的,其实是人与世界交互的方式,只要人的在神所定义的框架内行动,就必然是和谐的。这也确保了不同人所认识到的世界的统一性,从此,人类理性获得了与世界交互的权利。这也是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之一。当然,这只保证了人的感觉经验是真实的,但不能保证是整全的。
由于“单子之间没有窗户”,所以单子只能够认识到世界表象,又因为单子是独特的,其认识世界的方式又是前定的,所以单子认识到的世界表象实际上是自我认识能力的显现,认识世界归根结底是在认识自身。
伦理学和神学观点
虽然莱布尼兹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但他的生活环境和宗教背景使得他无法采取斯宾诺莎那样近乎无神论的激进立场。同时,笛卡尔的本体论也是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切都在上帝的干预下进行,于是人们无法给自身的行为提供一套包含基于“自由意志”的解释。于是,作为一个形而上学家,他必须在一个有神论的本体论背景下提出一套伦理学体系,来建构社会秩序。这套体系必须是调和的,特别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调和。
莱布尼兹的方案是“前定和谐”体系。这个体系有三个核心要点:
- 确保了上帝的意志得到体现,一切单子的存在和行为都必然是符合上帝的。
- 给自由意志留下了空间,上帝并不是直接规定了事无巨细的一切,而是通过环境或者既往的状态给予一种行为的倾向性(比如将某种行为定义为善)。
- 上帝是道德的,因此祂所确定的当前世界必然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个,一切所谓的“恶”并非是上帝故意赋予的,而是被造物不够完满的体现,也是用来衬托和凸显真正的“善”。
如果抛弃宗教的部分不看,莱布尼兹的“神正论”或许揭示了某种真相,即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当前的世界或许已经是最好的那个,或者说,是历史运动过程中,唯一可能的那个。
正如前文所说,“前定和谐”所“前定”的,是单子与世界的交互方式。因此,无论单子如何运动,都落在了和谐与善的范围内。但这样实际上就消解了“恶”的概念,其实就是教父哲学“恶是善的缺失”的另一种说法——“恶只是没那么善”。《神正论》的辩解就像神创造的世界那样完美,已经是宗教体系下所能给出的最好的解释了,唯一不那么完美的地方就是无法说服人。
黑格尔这样评价莱布尼兹的体系:“思想前进到什么地步,宇宙就前进到什么地步;理解在什么地方停止了,宇宙就停止在那里,而神就在那里开始了;因而有人甚至认为理解是对神不好的东西,神由于被理解,便被往下拉进有限性里去了……神仿佛是一条大阴沟,所有的矛盾都汇集其中。”
莱布尼兹竭力想要证明他的这套体系中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但他无法否认的是,相比于人,神依旧是具有统治性力量的。莱布尼兹的自由,其实是高等级单子(人类理性)面对低等级单子(物质单子)的强权。而且,在这套系统中,上帝单子实际上是被普通单子所回溯性建构的,普通单子的存在使得其必然需要一个上帝单子在其背后做支撑,上帝单子不得不被迫在一切单子面前现身。因此,上帝单子是唯一没有自由的那个。
莱布尼兹已经很努力地在调和信仰与理性之间地种种矛盾了,但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极限,因为形而上学是缺少反思的。形而上学从来都是“如果我的体系成立,那么……”,但是无法说明“我的体系凭什么能够成立”。形而上学永远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完满的形而上学存在究竟是为什么需要以一种不完满的物质世界的形态呈现。从完满到不完满意味着这个完满存在本身就蕴含的一种自我撕裂的不一致性。
评论区